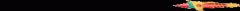卧底医院,揭的不是黑幕,是成见
2019-09-21医疗纠纷 编辑:admin
卧底医院,揭的不是黑幕,是成见
六六分别以患者和医生身份 “卧底” 上海的大医院半年,试图去揭开中国医患关系恶化的根源。
她的结论并不一定正确深刻,但为观察医患矛盾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与体验——理解医生。而有的观点认为,如果不能建立良性的医疗机制和制度,单靠 “理解” 并不能真正解决医患冲突。
由于医患冲突激烈,深圳市的山厦医院医生护士,一度戴钢盔上班。 (CFP/图)
六六 知名女作家、编剧,代表作《王贵与安娜》《双面胶》《蜗居》《心术》。
打破对医生的成见
2007年对我是很糟糕的一年,母亲被检查出乳腺癌。
术后很久,我和母亲都在讨论这个手术的意义。母亲在手术后活动起来,经常胳膊疼。她甚至一度怀疑这个手术是否真的必要。
而我不仅仅跟母亲讨论,也跟不同的医生讨论。我惊奇地发现,不同的医生对这个手术的必要性有完全不同的见解。
一部分人认为乳房对于我母亲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已经失去意义了,而生命高于一切,割除是最安全有效的方法。
另一部分医生则认为,这么早期,近乎零的癌细胞,局部清扫一下即可,创伤小,人活着不仅仅是生命,还要注重生命的质量。
给予我不同信息反馈的两派医生,全部都是我的朋友,忠诚可靠,不涉及利益。
于是我知道,排除在床位、红包、回扣等等之外,医生本身之间在同一病例上都有不同的理解。
医生是这样一个行业:它不是ISO9000标准管理系统,它全凭主观和经验。即使有先进的科技保驾护航,但在治疗上,依旧以个人判断以及对医学的认知水平为基准。不同的人,标准截然不同。
因此我有理由相信,我们对医生的了解,很肤浅,很片面,大多来源于报纸媒体等的宣扬,我们张口提及的都是医疗事故、掩盖、医药代表、过度医疗等。
2008年夏天,我母亲又被查出有脑瘤。
这里我要提到一位医生,他姓孔,是在我母亲第一次动乳腺癌手术的时候结交下的医生。
母亲对他几近于迷信,无他,他在母亲这里有权威,且愿意担当起医生的责任,是他替母亲做出决定不要化疗了,因为化疗对极早期癌症来说意义不大,还伤身体。他的一句:“你相信我,出事我负责!”让我们从此坚定地跟他走。
我母亲一次去见他,跟他说自己三叉神经疼,孔医生对母亲端详半天,建议母亲去做个脑部检测,他说:“我怕里面不好。”
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母亲大约是几年前起,脑部生长良性肿瘤,现在长大压迫面部神经了。
母亲在上海华山医院接受了第二次手术。
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大名鼎鼎,赵本山的脑溢血就是在那里治好的。我又一次与医生打上交道。
医生的共性是,如果你只与他们见一两次面,你会发现他们大多冷面,难开笑脸,“冷漠”是第一印象。
他们说话谨慎,善用边缘词汇,诸如大概,可能,也许,百分比。当我开始设计《心术》这本小说的时候,曾经想将这所医院的院长设计为反面典型。
带着探究黑幕的心理进院,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从院长到所有的医生,敢于敞开门让我进去看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能写的黑幕,早就被写完了。
最差不也就写那些吗?
你该怎样信医生
最终促使我走进医生的世界,从一个病患家属的眼光转为医生的视角,是缘于我偶然病倒住院。
人在虚弱的时候,我发现是最悲观失望对一切产生怀疑的时候,我把医生当作精神寄托,也不断质疑他们每句话的潜意思,他们是不是暗示我,我已经病入膏肓了?
他们是不是故意把我的病说得很严重,以方便榨取钱财?我在负面情绪中摇摆。
等我转危为安以后,决定走进医生的世界。我被医院同意,以一个医生的身份,走进了医生的世界(约半年)。
一天,我和吴教授出台会诊。我坐在吴教授身后,听某女病人如下对话:“医生啊,我们那边的医生让我过来看看,说我有垂体瘤,麻烦你给看看。”
吴教授:“你没有垂体瘤,CT里没有任何明显指征说明你有垂体瘤。”“可我为啥不怀孕呢?”
“这个你要问妇科大夫。”“妇科大夫说了,我不怀孕是因为长了垂体瘤。”
“可我说了,你没有垂体瘤。你相信我还是相信她呢?”“我不是不相信你,可我要是没有垂体瘤,为啥不怀孕呢?”
“同志,你到底希望长瘤还是不希望长瘤?”“我不希望。”“那我跟你说了,你没有垂体瘤啊!你去妇科再看看。”
……
那一个下午,吴教授需要这样鸡生蛋蛋生鸡地解释给病人很多遍类似的问题。人对于医生的信任应该怎样才能够建立起来呢?
去年我摔断胳膊,医生告诉我有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保守治疗,让骨头长在胳膊里,缺点是有可能以后阴天下雨疼痛。另一个是开刀治疗,取出碎片,缺点是有可能损伤运动神经。
正常情况下,医生会说:“我告诉你两种后果,你自己决定治疗方法,我不能替你做决断。”
这个医生我信任他,我让他替我决断,他最终让我不开刀保守治疗。
我的信任,为我省了一刀的费用和疼痛,且保护了我的运动神经。目前为止没出现下雨疼痛的症状。
他因我的信任而担负了责任。这就回到了一个问题上,你该怎样信任一个医生?信任一个人,就这么困难吗?
医生的委屈
在医院时亲身经历这样一件事。
有个孩子,五岁,病毒反复感染角膜,视力迅速下降,一周前还0.8,到眼科的时候就只剩0.1了。
那天接待他的医生是小波。小波和他素昧平生,一听说这状况就急了,带着这个小孩楼上楼下地跑,要最快时间做出各种诊断,尽早手术。
我是跟着后面楼上楼下地跑的。做到一个房角测试检查的时候,小波刚推门,有个七十多的老头就拿拐杖撑住门,说,你们医生就是这样腐败的,利用职权,老是插队!那要我们拿号干嘛?
他一说,群情激愤。
小波只好解释说,这个小孩只有五岁,马上就要失明了,要抢时间。
老头说,我们这里哪个不是要失明的?我们为做这个检查,哪个不是排队好几个礼拜的?谁都不能插队。
小波解释说,你能等,小孩不能等。
老头说,谁都不能等!疾病面前人人都一样。
我当时真想煽他耳光。我一气之下一把拉过老头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看不见有什么关系?他才五岁,你七十多的老头跟个小孩计较?”
老头拿拐杖打我,要不是小波拉着我,我肯定就煽过去了。
你们没见到那个孩子,不知道他多可怜。你不拉他的手,他就会顺楼梯滚下去。后来小波跟老人说,你先看,你看完了我们再看。
老头一本正经地说,我就是维护正义的。我不看,我看在这里,大家都看完了我才看。
我的眼泪当场就下来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对小孩子这样投入情感。也许是自己有儿子,不忍心看小孩受罪。小波说,以前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他为此难受了很久。
有个小孩做手术,排队排得一点一点视力弱下去,手术前一天晚上还能数清楚几个灯泡,第二天上了手术台,又撤下来,因为完全没视力了。
对小孩而言,时间就是视力。他到现在都在自责,如果当天晚上加班给他做手术……
所以我非常理解他这次为什么如此投入,其实是在弥补过去自己的内疚。
我们总拿放大镜挑剔别人的缺点和过失,却对善良和恩惠坦然受之,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恩,就是这样毁坏的。
医院的信、望、爱
我在手术室遇到个我以为要死掉的男人,全部的人都觉得他不行了。
但医护人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后关头奇迹发生。这个人在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抢救后,救回来了。连医生都擦着汗说:“他命大!”
所以我希望病患家属,对医生要多些感恩,少些责难。要知道,神明再保佑,医生放弃治疗,管子一拔,啥都没了。
在医院呆的这一段,让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无论你病患家属什么态度,医生护士再委屈,内心里是有杆秤的,不会因为家属的不理解,纠缠,吵闹而放弃一条生命。
《圣经》上说,这世界有三样东西对人类是最重要的,FAITH(信),HOPE(望),LOVE(爱)。我认为,我能看到的对这三个字最好的诠释,就是医院。
我曾在手术室里看见医生一针一针缝脑膜,这是一门几近失传的手艺,因为费时又费力,大多数人都用人工脑膜贴上当补丁完事。
我问他你为什么做这样的活啊!他答我:“我练手艺,艺不压身。”
后来熟了以后,我知这位病患来自福建山区农村,年收入都负担不起这台手术,一块脑膜要八百多元,他用自己的时间和手艺,替他省了。
他做这样的好事,躺在病床上的病人,永远不会知道,新闻媒体也不会报道他的善心。如果恰巧不是我站边上,又多话好问,这样的事就湮灭了。
他和他的同事们,每个月都在为付不起医药费逃跑的人们垫资。
如果我们有非常完善的健保制度,药品公平竞争进入市场,由病患自己选择,医生只有处方权而没有推销权,国家提高医生问诊的待遇和专业技能的待遇,而药物因渠道畅通价格低廉,医保局不是只下拨医院固定的数额,余额让医院自己补齐解决,
那么,我们或许就能从医生和病患的直接对抗中走出来,就不会再把原本属于制度的问题,直接推及到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上去。
态度决定医患矛盾?
我在医院碰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医生,一度颠覆了我对医生的全部判断。
他是医院里处理医患纠纷的院长办公室主任,他本人也是一位医生。
他跟我说,你写的小说都是浮在表面的,我告诉你一个事实:60%的医患纠纷,责任都在医院。
这句话对我实在是太震撼了!他说,病人到医院来是干什么的?看病的。谁吃饱饭没事干,到医院来吵一架弄点钱花花?
病人来闹,就是因为医疗不顺利,就是有问题。什么样的问题?我认为是态度问题。
有的时候的确是医生的责任心不够,疏漏;有的时候是态度不好,解释不到位;有的时候是给病人的期望值太高,最终没达到。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医生的问题。
他说,你各个医院走一走,大部分医生可能职业生涯里都会有被投诉的经历,但经常被投诉的,就那么少数几个。
我一直认为这就是害群之马,就是这几个人坏了医生队伍的素质。他们没有责任心,没有同情心,没有怜悯心,把病人当机器,把自己当操作员。
他们的口头禅就是工厂产品都有2%的次品率,我们医生一天都看一百个病人,怎么不能错两三次?
有这个态度放这里,他就不配当医生,这和你待遇高低、公平不公平没有任何关系。你增加了病患的痛苦,你拉长了治疗的过程,你多花了病患的钱,你就是坏人。
他说,我工作一生,门诊一天看病八十个以上,每个患者一到两分钟。我的手术也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没有一个病人投诉我。因为我以心换心。
病人进门,你冲他笑一下有什么难的?你的说话语气加一个请字,有什么难的?来看病的人,你当他们都是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小孩,你会这样呼来唤去居高临下吗?
他说大部分病患都是通情达理的。你工作做到位了,他们大多能够理解。他们要的也就是一个平等对待,争的是一口气。
他的说法,被我在医院里当“卧底医生”的那段经历验证了。对于一个完全没有医学背景的人来说,我起到了甚至连医生都起不到的作用,这是令我极其诧异的。
病患是病急乱投医,他们只要看到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和善的面孔,挂着照片和名牌,就会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地倾诉。
我的医生朋友们在解决完他们的工作以后,便将这样一部分病人转移给我,我的功用就是出借耳朵和同情心再加上温存软语。
我抽出相当一部分时间听他们说疾病的起源,家庭的纠纷,老板的残酷,未来的担忧,甚至房贷还有多少没还等等,听到动情处,我会提出我的意见甚至给予拥抱。
在我离开医院以后的好几个月,还有病人跟人打听那个“张大夫,人特好”。
所以我尽量地告诉医生朋友们,你如果换一种柔和的语气,多说哪怕一句关爱的话,病患和家属,都对你恨不起来。
重新建立起一种良性循环,一定需要有一方,先伸出手来。相对而言,可能医生更简单。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心术》,我希望它可以为双方打开一扇门,架一座桥,从相互怀疑敌视,到相互换位理解,尽量去信赖这个世界,我们就能增加安全感,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