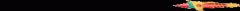“陪读小镇”上,那些被高考神话捆绑的妈妈们
2021-06-12百姓深思 编辑:admin
“陪读小镇”上,那些被高考神话捆绑的妈妈们
校园的铃声,不仅指挥着学生们的生活,也在为妈妈们的生活立法。
上顿渡不大。如果二环路上的北京城墙还在的话,把上顿渡放在里面,差不多能圈下。从全国范围看,这是个再平凡不过的小镇;但在江西, 这是个诞生神话的地方——关于教育的神话,说得再准确点,是临川中学的高考神话。
上顿渡最有名的是镇上的两所学校,临川一中和临川二中。前者在2021年《全国百强中学》榜单中排名43名,江西省排名第一。几乎每年,都会有数十名毕业生从这里考入清北。近二十年来,这两所学校吸引着来自江西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学生。教育拉动了上顿渡镇乃至临川区的经济发展,甚至连小镇上的潮汐昼夜,包括大多数店铺的开关张时间,皆以学校的铃声为示。
镇上最多的是两种人,一种是学生,一种是学生的母亲。陪读,是后者到此落脚最重要的目的。照顾孩子之外,多数妈妈还会去超市、房屋中介和手工作坊谋一份生计。但千万要紧的是,不能耽误自己的“本职工作”。陪读妈妈几乎能渗透上顿渡的所有角落。上顿渡年纪轻一点的女性“80%都是陪读妈妈”——有人甚至会这样说。
但现在,妈妈们在离开。只消在镇上逛一圈就能发现,房东们的空房间多了起来,有些商铺也贴上了关店转租的告示,地产商新建的楼盘不少陷入滞销。
随着几所中学的搬迁,上顿渡作为一个“陪读小镇”的辉煌正在消散。
但“陪读”不会消失。就在临川一中实验学校的新址,与上顿渡的衰落同时发生的,是一个“新上顿渡”的建立。“状元楼”、辅导班、小作坊、棋牌摊,正在这片名为“白岭新村”的农民自建楼里生长。7点、12点、17点半、22点,是学生上下学的时间,这些数字因为学校的铃声在白岭新村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陪读妈妈随着孩子迁徙至此,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呼吸。
神话
上顿渡据载已经存在千年。相传,此地始建时原名“顿溪”,为溪岸顿居之意。千年以来,宜黄河从这里穿流而过,让这里成为一个建有商驿、会馆的古渡。
古渡早已不在。今天,这里的活水是学生。与之顿居于此的,还有陪读的母亲。后者有一个特殊的名字——临川孟母。
新时代的孟母来自抚州乃至江西其他地市,甚至全国各地,她们像水一样流进顿溪,让孩子汇入高考大军。其目标是临川的两所中学,临川一中和临川二中。
赵引娣在上顿渡生活了73年。在她的记忆中,一中和二中几乎是上顿渡存在最久远的建筑,连县政府都比它们建得晚。她住在临川二中西门对面一条巷子里,拐出去,就是上顿渡老街。赵引娣说,上顿渡原本只有这一条大路,贯穿南北,一中在北头,二中在南头。
“才子之乡”是个当代神话。在包括赵引娣在内的不少上了年纪的上顿渡人看来,一中和二中经历了一场“爆红”,在那之后,上顿渡才渐渐与“才子”捆绑在一起。
这两所中学首次登上新闻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彼时,“超常教育”的概念炒得火热——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设立少年班,招收少年大学生。1977年,以13岁年龄进入少年班的宁铂正是来自江西。有统计显示,1982年至1986年,抚州地区先后为中国科技大学等九所高等院校少年班输送了66名学生,其中34名来自临川。一时间,小镇因“神童”喧嚣起来。在赵引娣的记忆里,这些少年大学生们考入的大学叫“少年科技大”。
另一个关键的节点是2002年。
新世纪初,临川区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抚州市临川区时任区委书记尧希平2002年接受采访时坦言,当年的财政缺口约有8000万,2001年则为7000万。在此背景下,区政府对临川一中、二中“财政‘断奶’”。两所中学就这样被推入市场。
2002年,临川教育集团成立;2015年,集团内的抚州一中、临川一中和临川二中又以“名校带民校”为由,分别建立了民办的实验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这种双轨制赋予了教育集团在现行教育制度下更高的自由度与自主权,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外地学生,而这些外来者们也成就了今天的上顿渡。在2007年的报道中,时任临川二中行政办主任熊海水回忆,从2002年开始,两所中学开始大规模涌进“外籍”学生。
2009年,临川一中新校区建成。随着新校舍拔地而起的是东西南北进十座住宅小区的落成,它们的名字也多有“文气”——学府世家、书香门第、状元府邸;甚至还有处楼盘取名“诺贝尔”。那是临川楼市最火爆的几年。一位曾给外地生们做过几年保姆的本地人告诉全现在,学校南门的文鼎苑楼盘,开盘后没出一周便全部售罄。
赵引娣住的是一幢三层民房,一墙之隔,就是2018年建成的高层楼盘。新开盘的房子,一平米价格近万。紧挨王安石公园的“丽水豪城”项目的房产中介告诉全现在,目前该楼盘现房价格为5680元每平,只剩两套在售,其余皆已售罄。她说,开发商的总经理来自河北藁城,正是瞄准了上顿渡因学校带动的市场,才在此投资。
赵引娣家原有的耕地被征去盖了新楼盘。她就用补偿款另建了一幢小楼,一层堂屋,二层自住,三层是两对二中的陪读母子,在上顿渡街头,经常能看到地产商的广告,“让孩子赢在人生起跑线”。标语和它所构建的高考神话,堆叠在上顿渡,编织着有关未来的梦。
陪读
对于购房者来说,买房,就是为了上顿渡的户口;有了户口,才能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25岁的李娜和母亲在上顿渡经营一家手工作坊,生产塑料发夹。平时,她一边看店,一边照顾三个月大的儿子。虽然儿子年纪还小,但她已经在为陪读临川一中做着准备。几年前,她和在抚州市做电梯维修的丈夫买下了镇上一个新建的楼盘,为的就是给儿子落户。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就进入临川的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才有更高的几率升入镇上的高中。她告诉全现在,临川区的户籍政策这些年一直在变,现在买下房子后,需要七年才能正式落户。之前,这个时限是5年,再之前是三年。有了户口,孩子才能进入临川的九年义务教育学校。为了一个确定的未来,他们得提早准备。
“(来)我们这儿的都是陪读妈妈”,李娜说。她的小作坊位于老街东侧一片安置房的三层楼群内,这片区域里,类似的小厂还有很多家,除夹子之外,还分别会制作手套、头绳等小物件。空闲时,妈妈们会到作坊里打点儿零工,要是住得远,还可以把“料”拿回家里。
在李娜的作坊里,做一件夹子能赚一分,老板净赚2厘。“妈妈工”是产业链的最低一环,这些产品从她们手中离开后,还会经过三四层中间商,最终到达浙江义乌。李娜透露,像这种义乌小商品,源头的制造者,都是四线或以下城市的妈妈。一天下来,一人大多能挣二三十块,这对每月平均三千元上下的开销来讲是杯水车薪。“打发时间”,是这份工对妈妈们来说最大的意义。

“妈妈工”们在李娜的作坊里做活。(左一为唐丽)
店里三四张小桌,每张桌子旁都坐着三名女工,手工活在掌间上下翻飞。“当陪读妈妈的感觉?枯燥呗!”唐丽说。她今年39岁,临川本地人,三个孩子,两个读小学,大女儿在临川一中上高二。唐丽的丈夫一直在广东做建筑工,独自陪读的生活,她过了十七年。
下午是小作坊最忙的时候,因为上午孩子去上学后,妈妈们需要准备午饭,午后到晚上这段,是她们可以自由支配的最长也最完整的时间。唐丽身材微胖,发丝间渗着些汗水,她坐在桌子一侧,从塑料堆件中拿出两粒,再取根小针,夹着镊子推进孔里,不消几十秒,一只发夹就能做好。这是个做不完的工作,原料总要做完再取,成品堆满即清,两堆碎料块此消彼长。
唐丽的生活就淹没在这种无休止的重复动作中。除了这份“死累”而又收入低微的活计之外,她每天还要按时洗衣煮饭,照顾好孩子们的后勤。她羡慕丈夫的工作:“在外面打工多好,一门心思赚钱,赚到钱就下班,下班就睡觉。”
李娜从不愁生意。手工业时间灵活,工资计件,是妈妈们的理想工作,妈妈工“毕业”一批又来一批。她有时在抖音上分享一点作坊里的生活,总有人在下面评论:“哪里拿货?”
“你到街上去看,见到年轻一点的女性,你上去问,80%都是陪读妈妈。”在镇上生活十年,李娜能感觉到,来陪读的年轻妈妈越来越多,陪读年限也越来越长。她告诉全现在,在以前,上顿渡的陪读模式是,小孩中考达到临川一中二中的录取线后,家长带着孩子到镇上陪读;大概从六年前开始,越来越多的妈妈会在孩子上初中,甚至小学时就来到临川。
“现在的人思维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嘛,人都往热闹的地方走是不是?”镇上的一名网约车司机认为,“乡村教育,乡村教育能教育出什么来呢?出了名的才子校园才是更好的咯。”他的老家在临川区下面的村里,“现在村小都没人了,一所学校一个学生、三个学生的都有。还有的学生,上了一个学期就不上了,(家里)给安排到其他学校去。”
村小和县中的衰落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赢在起跑线,考到大城市,是包括李娜在内越来越多家长的想法。而要想让孩子成绩好,走出小镇,必须有一个人留下来,这个人通常是妈妈。
“自己不努力,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作为唐丽们的后备役,李娜已经在为教育发愁了。儿子出生前,她在武汉的一家国学教育机构里做过幼师。自认为见识过“大城市里的教育”,她不甘像同乡们一样将小孩送入村小,而是来临川落户。她看中的是这边优秀的学校资源以及更多的“体制外教育”——上顿渡街面上有不少课外辅导机构,包括舞蹈、口才、乐器等多种门类。
“一切为了孩子”被贯彻在上顿渡每一位陪读妈妈身上。校园的铃声,不仅指挥着学生们的生活,也在为妈妈们的生活立法。

中午,临川一中的学生们在放学路上。
中午十二点——这是临川一中午休时间,下课铃响,约万名学生会从学校涌出,在一个个路口分流,最终消失在上顿渡镇的大小楼房里。在那里,妈妈们备好了当日的午饭,到家吃完饭,再做些功课,就是孩子们的午睡时间。依照距离学校的远近,租房价格也各有不同。在临川一中南门对过的“文鼎苑”小区,一套房屋的一间卧室,最贵能租到一年两万;条件差一点的,会租一间车库,一年四千元。有的家长会为了让孩子多睡十分钟,选择更贵的住房。时间有它的标价。
一点到两点半,文鼎苑小区的小广场上,会聚满母亲的身影,这是她们“放风”的时间,也是小区最热闹的时候。有人打牌,有人闲聊,还会有妈妈坐在长椅上,掏出一兜白手套的半成品继续做活。虽然夜晚只能睡五个小时左右,但在中午,她们必须保持清醒。如果因为自己睡过头没能叫孩子起床,麻烦就大了。
捆绑
文鼎苑小区的小广场上,坐满了在打牌和闲聊的陪读妈妈。
张秀芬的儿子今年高考,她的老家在距离上顿渡百余公里的村里。2014年,女儿在小升初考试中考上了临川一中,她就带着当时五年级的儿子转学到了临川。至此,她已经在上顿渡生活了七年。之前,她在学校附近的超市做过收银员,儿子上高三后,她开始一心帮儿子备考。
张秀芬自称是“乡下人”,和镇上本地人不一样,她不会和人搭话,也从不跑到长椅上打牌。午后妈妈们集体“放风”的时候,她穿着条红色长裙,坐在广场边上划拉手机。张秀芬对陌生人总会带有防备,“在村里叫人骗怕了”,她这样解释。
这七年,她社交很少,就算在家里,也不敢多说话。临川一中学习压力大,她的孩子基本每天写作业都要写到凌晨一点多。张秀芬小学文化,儿子的功课插不上嘴,也害怕管多了生出事来。许多陪读妈妈都对全现在称,现在的小孩“不敢管”,因为“总有学生想不开”。唐慧每年都能听到这两所学校中有孩子跳楼的传闻。据报道,2013年9月14日,临川二中一名高三学生因不满严格管理,在办公室割颈杀害了自己的班主任。
在上顿渡,几乎每座楼的窗户都安着防护栏,在一间间笼屋里,妈妈们要陪着孩子度过数个春秋。缺乏娱乐,缺乏社交,更重要的是,“没有自我”——这是许多妈妈都会说出的话。而与此同时,她们也会认为“这就是妈妈的义务”。
在上顿渡,基本所有的窗户都装着围栏。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2020届本科毕业生万若六年中学生涯都在临川二中度过。经历过陪读的她承认,在陪读过程中,学生和家长的情绪都相当受到成绩影响。在这个名为“陪读”的空间里,母子双方都“被学习支配”着。在毕业论文中,她访谈了13名在上顿渡经历过陪读的学生。在她看来,“陪读家长对成绩的过分关注会给学生造成心理压力,其中成绩越好的学生压力越大,他们将家庭的高期望、父母做出的牺牲内化为自己的心理压力。”
“有的学生金榜题名,有的学生名落孙山,有的陪读家庭轻松和谐,有的陪读家庭矛盾重重,我们无法一以概之地解释这些差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拥有独立人格和思维能力的人,陪读需要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论文中,万若这样写道。
万若希望陪读妈妈能对孩子少一点关注,多一点独立空间。但现实是,大部分妈妈都则接受这种捆绑,将自己的生活全部寄托于孩子的每一张试卷。
2019年,张若兰关掉了老家赣州的服装店,因为她的女儿在初中毕业后参加了临川一中实验学校的自主招生考试,并且收到通知,获得了免费入读的资格——据家长间传言,这项待遇是考试前六十名的学生的专属。
张若兰就这样来到临川,在学校对面租下一间房子,开始了自己的陪读生涯。
在临川的高中里,班级被分为三等:零班、A班、B班。张若兰的女儿被分到了“零班”。在全现在接触到的学生口中,零班是“只能仰望的存在”。和其他班级相比,零班师资强、进度快,作业量和学习压力也大。一名高二学生称,零班的同学作业差不多要写到凌晨两点,就这样,第二天早上还要到学校补完剩下的作业。
在一中,成绩不仅划分学生的班级,还会划分家长的待遇。有当地人告诉全现在,在临川一中老校区里,应届高三生中成绩好的,家长可以在学校宿舍陪读。张若兰说,她女儿班上的老师都是华东师大毕业,年薪能达到二十多万,“A班B班什么情况我们可不清楚”,她带着些骄傲。女儿告诉她,班上还有位从北大计算机专业退学的学生正在复读。
“到这来就是冲着清北,不冲着清北跑到这干什么。”刚到上顿渡那阵,张若兰心气高得很。但高一的第一次月考,就叫她认清了形势。按照过往的录取名单,即便是成绩好的年份,也要年级前二十才有可能达到清北的录取线。女儿的排名在八十。
起初,她觉得是女儿偶尔没发挥好,但一年过去了,排名还是稳定在六七十的位置。女儿成绩提不上来,张若兰“一宿一宿睡不着觉”。表面上,她安慰女儿,“一两次考不好没关系”;但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她会默默坐着,断绝一切社交,还会挂断老公打来的电话。
她不会到家长们聚集的地方聊天,更不会去麻将摊上打牌——传言说,有个学生父母都来陪读,结果到了临川之后,父亲沉迷麻将,母亲沉迷广场舞,孩子甚至要半夜把爸妈从外面叫回来睡觉。娱乐,在张若兰看来,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张若兰坚信,今天的学习成绩就等于明天的人生命运:“你好好学习,你才能帮助更多的人。你自己也能过上人上人的生活,感觉上你就不会低了一等,然后你接触的人和社会都不一样的,人群都不一样。你说那些没读高中的孩子,慢慢的慢慢的,他接触的人的社会地位全部都不一样了。”
复制
2019年8月,张若兰经历了一次搬家。她从上顿渡搬到了抚州站前新区,临川一中实验学校的新址就建于此。学校对面,是一片名为“白岭新村”的农民安置房,随着学校和家长的到来,这座原本只有老人居住的小村热闹起来,辅导班、高考楼、小作坊一一开业。村里的快递点贴着的招牌都是“妈妈驿站”。
村里的“妈妈驿站”。
在这个距离上顿渡大约八公里的地方,“陪读小镇”似乎正在进行复制粘贴。
上午十点半,周桂霞正在村里的一家手套厂做工。这和上顿渡的那些小作坊并无二致,同样是由一座自建楼的一楼改造而成,几十平米的毛坯房里整整齐齐摆了十几台缝纫机。周桂霞的孩子正在读初三,学校从上顿渡搬到这里后,她也就换了地方陪读,但工种没换,还是做手套。虽然实验学校可以选择住校,但她还是在学校边上租了房子,“从生下来就自己带,一直这样子”。
周桂霞算了算,自己每天打孩子六点半吃完饭上学后就来缝手套,十一点多回去做饭,孩子下午两点上学后接着做手套。一天下来,她大概能做两三百个,一个两毛钱。
周桂霞工作的手套厂,和上顿渡的小作坊并无二致。
徐建龙也把之前开在上顿渡的辅导班“励志精品补习学校”搬到了这里。他自称在临川做了十几年课外老师,主要辅导地理和数学。由于妈妈们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徐建龙这类老师,正好迎合了家长们作业辅导的需求。他的“补习学校”开设两种班型,分别是作业辅导和周末补习班,价格依年级不等——高中学生的周末班价格为每学期4000元,作业辅导为每月1200元。
白岭新村正在变成下一个上顿渡,这也为这里的原住民们带来了财源。首先是房租。妈妈们说,学生们刚过来的时候,房租基本维持在每年一万六千元,后来基本每过两三个月,房东就会“坐地起价”。现在,最靠近学校大门的房子,已经涨到了两万四一年。有一些房子,还没完全建成,招租信息就已经贴了出去。广告上,“白岭”已经被写成了“白领”。
就连学校里也住着妈妈。全现在在临川一中实验学校传达室里见到了一位在食堂工作的陪读妈妈,早上6点打卡,晚上7点10分下班,一个月工资两千出头。她是抚州当地人,之前在上顿渡陪读,去年学校搬到这边,就在新学校食堂里找了份活干。她告诉全现在,在学校里,像她一样的妈妈还有很多。有家长称,有的妈妈为了边照顾孩子边挣钱,会到学校里做宿管,一天工作12小时,工资三千元。
肖彩慧是“白领新村”的新租客。临高考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肖彩慧回到了女儿周娜娜身边,在白岭新村租下了一间房,不到30天的租期,房东收了2600元。
女儿是“高四”的复读生,之前在南昌师大附中,因为高考成绩比估分低了近三十分,只能上南昌大学。周娜娜觉得“丢脸”,为了能进985,她选择再考一次。
因为高考成绩好,临川一中直接帮周娜娜办理了户口迁移和入学手续,还免除了学费。有家长称,为了能帮学校出成绩,学校会按照分数为一些复读生提供优待。临川一中实验学校的学生告诉全现在,校方会对尖子生提供优惠;而分数较低的学生,则需要按照排名划分等级,每学年收取6000至18000元的借读费。这名来自鹰潭的学生还向全现在透露,学校里不乏“大老板的孩子”,“十个(差生)养一个(尖子生)”,他这样形容。根据临川一中官方网站提供的数据,2021年临川一中收入预算总额为13654.11万元。
“我的快乐伴随着一次高考消失了”,周娜娜说,拿到高考成绩后,她几乎立刻就做出了复读的决定,“我希望我去年考高很多分,因为我这一年实在是太痛苦了”。周娜娜说,在那次高考之前,她并没有那么在意成绩,高考失利让她“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价值”,开始认为“成绩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在临川一中,学习压力来得更加实在。之前在南昌读书时,周娜娜高三下学期一共就只考了四场大考,但到一中以来,她数了数,他们高四的学生至少经历了15场考试。
她把这里的生活形容为“坐牢”:睡的是铁架床、食堂饭菜不新鲜,老师会强调“在读书的时间就只能读书”,“唯一的休息方式就是睡觉”,学生连出去散步都不会得到认可。
“压抑”,这是周娜娜林一生活最多的感受。她描述,住校期间,每晚12点上床后,闭着眼睛,直到凌晨三点左右才能入眠。终于,临高考前一个月,在女儿的要求下,肖彩慧来到了临川。
现实
在女儿复读之前,肖彩慧在南昌做过六年陪读妈妈。女儿上中学那段时间,在肖彩慧印象里,是家长和学生们最为焦虑的。
肖彩慧在手机里设了近十个闹铃,提醒自己按时完成作为陪读妈妈每天要做的事。
周娜娜的理想职业换了好几次,最开始是心理医生,后来是经纪人,最近复读的这段日子里又改成了金融,原因就三个字,“很赚钱”。
南昌师大附中周围同样住了很多陪读家长,肖彩慧自称是其中比较“佛系”的。在周娜娜的高中班上,学生和家长几乎时时刻刻都在为自己的孩子会不会“掉班”而担忧。肖彩慧称,女儿所在的师大附中“零班”的学生中,每一个都相当优秀,自律性极强。一旦因为一次考试排名不佳掉到普通班,学生和家长都会在那段时间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肖彩慧还记得,女儿高一时,一位同班女生在一次月考后从学校附近租住的27层楼上跳楼自杀。事件发生后,老师专门组织了家长会,据称致使意外发生的导火索可能是女孩的父亲缴掉了女儿的手机,两人大吵一架。几年后,那个学生的父亲,一名警察,也从自家楼房19层坠楼身亡。
比起有些全职的陪读妈妈,周娜娜觉得自己的母亲“做得不够好”。比如,有的妈妈会给孩子定好精确到分钟的每日计划,“几点钟到几点钟做什么事,全都安排好”;还有的妈妈是“消息通”,对于各所高校的师资力量,中学的补课情况,大学的专业报考都了如指掌。
“她70%的精力都用到那些小朋友身上了”,周娜娜说。肖彩慧在南昌经营一所幼儿园,女儿也是从那里升入的小学。周娜娜还记得,好几次,母亲送她上学,一张嘴,说出的都是“上幼儿园”。
也许是长期和年幼的孩子们待在一起,肖彩慧有些“心大”,把女儿也教得单纯。如果在白岭新村呆得再久点,融入了这里的“妈妈群”,她就能感受到什么是现实。
天黑后,陪读妈妈们在超市门口“打小牌”。
从天色刚刚擦黑开始,这里的街面就成了妈妈们的天下。给孩子送过晚饭,妈妈算是基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在孩子们十点放学之前,她们终于有了一段喘息的时间。这时,有些妈妈会结伴散步,老一点的支起牌摊打牌;稍年轻些的,则坐在了麻将馆前的凳子上,交流自己“陪神兽读书”的经验。
和上顿渡临川一中公立校的陪读妈妈们大多来自抚州本地相比,由于政策更加宽松,实验学校的妈妈们来自江西各地。对于她们来讲,陪读的成本更大,因此对孩子的期待也更高。
“我就把他(孩子)当投资,不管学什么,你出来不还是想赚钱?谁不想单位好一点,赚多一点钱,轻松一点赚钱?”“你看那个老师讲那个课,人家说了,就算你赚一辈子钱,说不定你儿子一年就给你消耗了。你这样来陪读,说不定你一辈子赚不到的钱,他一年就给你赚来了。”这是麻将摊前一位妈妈的发言,后半段内容来自于她在抖音看来的视频。听了这段话,她更加坚定了陪读这条道路,“都陪读,你不陪行吗?”
这个线下的“妈妈群”成员总共七位,大多是放下了生意来到临川,有些甚至是把孩子从浙江、上海带过来的。对于其中一些妈妈来说,陪读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我女儿原本放在县城中学读,后来看到不对了,别人都往(临川)这边跑,我也赶紧把小孩送到这边来。”还有妈妈说,自己初中小孩班上还有好几个从北京送过来的,要在临川读了书后再回去考试,“那边卷子简单”。
“今年江西高考考生多了3万人”,一个高三学生的妈妈说。一旁那位“把带娃看作投资”的妈妈立马搭话:“现在录取分数越来越高,怪就怪这些家长,再这么下去,分叫他们搞得越来越高了。”
还有位妈妈有点苦恼。最近,她的儿子突然问了她个问题:
“人活着,为什么要这么累呀?”
(除万若、徐建龙外,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全现在公众号呼叫转移,由“液态青年”接力,继续关注当代青年人的工作、生活和精神世界。
请搜索关注公众号:液态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