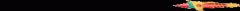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往事(点击原文1、原文2、原文3、原文4)
我在财政局工作的那十年(之五)首发2024-05-10 18:00·蒹葭碧风文/蒹葭碧风
清理工作才刚刚开始,我就感觉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
一是舆论的压力。清理“小金库”一开始,县直机关就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是财政局在揽权,显示高人一等;有的说,这是财政局长的虚荣心膨胀,意在让人仰之鼻息;有的说,这是财政局长的勃勃野心,是想吃“人血馒头”;有的说,这是财政局长耳聋眼瞎,看不透火候,书记、县长是“高举轻放”,他却傻帽不知,书记、县长“放个屁”,他却拿当“三眼枪”扛着。
二是上访的压力。以“小金库”账户将要被财政局冻结为由,有的单位向职工散布消息,说个人的奖金将被停发,撺掇职工到财政局讨说法;有的单位向施工企业散布谣言,说单位将付不出工程款,怂恿农民工到财政局讨要工资。
三是家庭的压力。自清理“小金库”以来,家里始终没断过来人,来的不是机关单位的领导,就是单位的会计,都说自己的单位“小金库”不能查、账户的钱不能收,如要查收,后果将如何如何等,总之让你家里不得安宁。
爱人对此深恶痛绝。我只有向爱人解释说,这是县里开了大会的,书记、县长都是讲了话的,这事怎么能不做?爱人生气地说,县里开了大会而没有动静的事多了,书记、县长哪天不在讲话作指示,下面当真的和实做的有几个?过几天清静日子不好吗?你明知道这是得罪人的差事,你还搞什么破改革。
四是威胁的压力。在清收某局300万元非税收入后,这个局的领导,就托人捎口信威胁我说,如果300万元不返回,就要带人修理我,并说要我腿断胳膊折。当然,我知道这是“黑诈胡愣抨”,我也没理,他也没来。尽管他没来,但我心里还是有一丝担忧,心里的“阴影面积”也着实不小。
面对“四面楚歌”,我找书记、县长求助,希望再召开一次清理“小金库”调度会。
可是,书记、县长几乎是一个腔调:此项工作,由你全权负责,少开会,多想点子;少请示,多干实事。
领导话里透出的意思很明确,工作还要搞,但不要把火烧到书记、县长身上来。
尽管领导有点往后缩,但我自己已没有退路,还得硬着头皮清下去。
不清理,财政改革就没法搞;不清理,书记的政务新区建设资金就没有着落。这惹人的事,领导往后缩咱没有办法,但自己是不能往后缩的,否则自己就只能当个“受罪”的局长,而且还不知道哪年哪月是个头。
这么重要的工作,又是得罪人的差事,没有县领导挂帅出征,小组成员似乎如泄了气的皮球,都不说话,精神消极,要么就说“局长你看怎么搞就怎么搞”,要么就说“要不然先停一段时间,再看看县领导的真实意图”。
他们还善意地为我担心,担心我这小身板,能否顶住这巨大的压力。
我心里明白,这是消极躲避。
组员躲避和怕事,可以理解,但自己得理直气壮。我说,此事不能停,还要继续,大家先把手头的资料整理一下,容我再思考完善清理工作方案。
而就在此时,县里出了件大事,县土地收储中心主任被“双规”了。中心主任被“双规”,揭开了“小金库”的惊人一幕。这一幕的出现,倒帮了我迅速推开财政改革的大忙。
县土地收储中心“小金库”私存的钱,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有1个多亿,这些钱都是截留县里的非税收入,其中土地出让金占大头,这是连县财政国库里也常常没有这么多的巨款。
可是,这些钱大部分被花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了两三千万。花掉的钱,有的是变相贪污,有的是滥发福利,有的是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当然也有小部分的正当支出。
此事反映到上面,省市领导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居然一个土地收储中心的“小金库”就存款惊人。省市领导的的批示,疾风暴雨般的落到了县里,要求县里举一反三,彻查“小金库”。
就在土地收储中心出事后的两天,县委书记出面了,安排纪委赵书记牵头召开县直部门一把手会议。
赵书记冷峻的表情,足以让台下不寒而栗,会场鸦雀无声。他代表县委严厉地指出:谁不配合,就处理谁;谁拒绝清查,就免谁的职。
这样一来,清理小组迎来了全面查账的大好局面。一个地方社会风气的好坏全在当地党政一把手。只要党政一把手自身廉洁奉公,手下就不敢胡作非为。但是,由于反腐越反越腐,导致如今暗中诱导、渎职、自身贪污堕落,造成有良知的官员信仰崩塌,老百姓怨声载道的党政一把手越来越多,以致无官不贪.......。
我趁热打铁,连夜召开了清理小组全体人员会议,并邀请县人民银行和八大商业银行行长参加。会上,我宣布了完善后的清查方案:
一是发放清理“小金库”申报表,表内填报开户行、账户名称、资金性质、资金额度。报表由各单位主动填报,并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哪怕是单位没有“小金库”,也要实行零报告。
二是由商业银行提供各单位所开账户明细,用于与各单位申报表进行比对,并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实事求是,不得瞒报漏报,否则县财政局将采取惩罚性措施,取消其财政代理业务,撤销财政账户、划走财政资金。
三是“小金库”中所有资金,按资金性质全部划入财政指定的账户。
四是“小金库”清理完毕后,商业银行要配合财政局全部撤销“小金库”账户。今后各单位要设立账户,必须报经财政局审批。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小金库”清理工作异常顺利,再也没有之前的那种鸡飞狗跳、乱哄哄的场景了,各单位都主动申报,都把“小金库”视作烫手的山芋,恨不得早点交出去,以防引火烧身。
临近年底,“小金库”清理工作也已临近尾声。初步统计,全县清理出“小金库”资金大约有1.5亿元。
凝视那报表中的数字,先前那种枯燥乏味的感觉已荡然无存,随之而来的是那数字之美,美得让人窒息,美得使人兴奋。
恍惚中,我似乎望到了国库中哗啦啦的钞票,仿佛听到了政务新区建设的机器轰鸣,又依稀看到了书记、县长满意的笑容。
那一年的冬天,好像比往年来得早一些,刚进入12月份,就落了一场雪。
在那场雪的傍晚,局里的人都早早地下班了,我独自在二楼的走廊里,斜倚栏杆,感受着小院少有的宁静。
静静地看那墙角的腊梅,静静地看那无声的落雪,静静地听那寒风穿过小院,静静地感受着数月来喧嚣之后的美好。在那片宁静之中,享受着内心的波澜不惊。
12月31日,是财政局的不眠之夜。
预算、国库等股室彻夜灯火通明,都在加班盘点一年的收入和支出。据姚副局长介绍,像这样的夜班,每年这一晚都是如此。
我坐在办公室里,等待着在预算、国库等股室送来的各种报表上签字。
当看到当年的收入达到1.8亿元,同比增长35.8%这组数据时,我非常高兴,这是多年来增幅最大的一次,着实为自己年初的建议被县长采纳而高兴(采取给予国地税超收奖励的举措)。
当看到清理“小金库”资金锁定在1.67亿元时,我兴奋得像孩子一样跳了起来,转圈挥舞着手臂,像范进中举一样癫狂,嘴里不停地念叨,“有钱了,有钱了”。
整个人都沉浸在无比快乐和兴奋之中。这样的快乐和兴奋,注定是今夜无眠。
时钟指向零点,2009年悄然而至。
姚副局长过来汇报说,所有的掐账工作都已完成,可以吃“年夜饭”了。
那顿晚餐,同志们都很高兴。我向大家敬酒,感谢大家的鼎力支持;同志们也一杯复一杯地向我敬酒,祝贺我艰难脱困,在困境中取得阶段性成果。
会计核算中心的高主任开玩笑地说,很惊诧你这个看起来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也会有如此的担当和魄力,竟使出这般霹雳功夫,这是大家没想到的。
高主任的调侃,让大家都笑了起来。
那一晚,我喝醉了。(未完待续)
乡镇往事(11):管家老纪(点击原文)
说老纪是管家,其实老纪就是个镇里打杂的。
我在潼楼镇工作期间,结识了老纪,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5年6月,我到潼楼镇任镇长,在刚到任几天里,经常看到一位年长的男人,经常去给我办公室送水,每次送水后,都是一声不响地离开,我当时怀疑此人是哑巴。
有一天,办公室白主任到我办公室来汇报工作,我问给我送水的那个人是不是哑巴?
白主任大笑说:“谁都能是哑巴,唯独他不能是哑巴,与他说笑,话永远不会掉到地上。”
随后,白主任向我介绍了老纪的一些情况。
原来,老纪不姓纪,老纪真名叫李纪祥,镇里的人都叫他老纪,他的真名早已被人淡忘了。
叫他老纪,是因为老纪性格耿直,办事较真,镇里的一草一木,谁都别指望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往家里拿。人们都戏称他是纪委干部,随后镇上的大人、孩子都管他叫“老纪”。
老纪是潼楼村人,就住在潼楼街上。老纪何时到镇里来的,现在镇里没几个人说得清。
据说,老纪初中毕业后,在部队里当过几年兵,退伍后,在村里当过两年民兵营长,再后来就在潼楼区公所里来打杂,一直到现在。
老纪,主要职责不单是打水扫地,还负责跑通知(那时电话还未普及,镇里下发通知需骑自行车去通知)、夜间值守、修理水电、保管物品等。
接触时间长了,才了解到,老纪非常健谈,但很有眼力见,能分清场合,平常从不多言多语。闲暇之余,一旦打开话匣子,他那不失风趣的话语,如流水一般,细细地流淌。
我在潼楼镇工作五年半,他给我的感觉,不像是50岁的人,倒像一个60多岁的人,两鬓斑白,满脸皱纹,但身材很结实。
可他这副面相,好像被冷冻了一样,似乎总是一个模样,仿佛他不曾年轻过,也不曾变老过。
他不穿别的衣裳,终年穿着从部队退下来的黄军服。人们不曾见过他分外地高兴或者忧心,他默默的神情总是那样和蔼,眼睛时常眯起来,眼角那儿的皱褶深深的、弯弯的,隐约着静静的笑意。
那时,乡镇的夜晚是很寂寞的。镇里的干部大多是当地人,有的住在镇政府的南院,有的住在街上。傍晚下班后,镇里干部都回家了,院内常常就剩下我和老纪。
那时的乡镇条件差,书记镇长的房间里也没有电视、空调,所配备的电器,就是电灯和电风扇。
冬天的夜晚,我就早早地钻进被窝,围被看书,看困了便睡觉。
夏天的夜晚,房内酷热难耐,电风扇越扇越热,倒不如院内凉快。
于是,我时常到院内,一边乘凉、一边与老纪闲话。时间长了,彼此便形成了一种默契。
每当我吃罢晚饭,处理好办公室白天送来的文件后,端着茶杯走出房间时,准能看到老纪已坐在院内那长条椅上等我,面前茶几上放着茶水瓶,他不时地用手电筒照向四周,观察周围是否有异常。
夜晚,院内特别地安静,四周一片漆黑,只有办公室射出一束的灯光,显得特别光亮。
我俩静静地坐在长条椅上,一边喝茶、一边抽烟,一句没一句地、天南海北地闲话。
从闲话中,我了解到老纪的家庭比较困难。家里总共不到三亩地,收入微薄;老婆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家中有两个儿子,老大已外出打工,老小在镇上中学读初中。家庭开支,全靠老纪每月在镇里帮工的300块钱。
为节省家庭开支,老纪还经常去镇食堂里帮忙,食堂师傅看他勤快,就送他一些剩菜剩饭吃,有时还送他两杯酒喝。
从闲话中,我有时还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镇里的干部,谁跟谁是二乔,谁跟谁是亲家,谁跟谁关系好,谁跟谁有矛盾,谁办事利索,谁办事拖拉,等等。这些情况,是我平时难以掌握的,这对我指导工作很有帮助。
有时,老纪也讲一些乡间轶事传闻。
有一次,他给我讲了一个“听文生义”的故事,很有意思,几十年过去了,我仍记忆犹新。
他绘声绘色地给我讲了如下的故事:
说“文革”期间,他村里有个生产队长,是个文盲,但脑子好使,记性好、悟性高。
有一年冬天,区里开会,先是安排冬季农田水利工作,然后传达了最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散会后,队长当晚就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召开社员大会,向社员传达区里的会议精神。
队长有样学样地传达了冬季农田水利工作后,也传达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一最高指示。
传达后,有位社员站起来发问:“队长,你最后传达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队长你给解释解释。”
队长愣了一下,心里也不解其意,半天说不出话来。
队长心里默念着“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脑海里急速地盘算着该怎样解释。
忽然,他想到今天区里的会议主题,是冬季农田水利工作,肯定这段话与今年的冬季农活有关。
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胸有成竹地解释道:
“深挖洞,就是说上级要求我们广大社员,今年冬天要把留作春地,都深翻起来,冻它一冬天,明年一开春,土壤就会更加松软;
广积粮,就是说上级要求我们广大社员,今年冬天一定要大干,不是一般地干,而是要甩老掉棉袄,光着脊梁干。”
队长说到这儿,略加停顿,想抽口烟,可是那位社员紧追不放,接着问:“那不称霸又是个什么意思?”
队长鄙夷地瞟了一眼那位社员说:“你是猪脑子?你想,土地经过深翻,又经过一冬天的大冻,来年春天土壤已经松软,还撑得起一耙吗?这就叫做不称霸。”
这番“听文生义”的解释,让社员都信以为真,认为队长的水平就是高。
说老纪性格耿直,办事较真,真是名不虚传。
办公室白主任对他非常信任,办公室里的信纸、笔墨、笔记本,甚至连救灾物品都放心地让他保管和发放。
像发放信纸、笔墨、笔记本这样的小事,他都做得滴水不漏。他自画了一张登记表,无论大小干部,谁领,谁必须在上头签字,并且,每次只能领取一本、一支或一瓶,用完再领。
有一件事,更是凸显老纪“纪”的本色。
有一次,老纪发现自己保管的原“潼楼区公所”的牌子不见了。
原来撤区并乡后,大门口那“潼楼区公所”的牌子被“潼楼镇人民政府”牌子取代,那区公所的牌子质地好,是楠木的。
领导交待老纪,这块牌子将来是文物,很有历史和收藏价值,要好好保管。
老纪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他经过多方打听,得知这块牌子被刚退休的老郝扛家里去了,用来在床下放鞋子。
他二话不说,径直穿过大街,跑到老郝家里,从床底下捞出,扛起来就走,当时搞得老郝很不好意思。
甭看老纪是个打杂的,我与他闲谈中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有些信息是开座谈会和找班子成员谈话得不来的。
比如,我发现镇里的每月招待费都居高不下,但不知原因。
有一天晚上,闲谈中,我问老纪。老纪神秘一笑说:“在食堂接待,招待费不会高,高就高在外面饭店接待。”
我说:“在外面饭店招待的价格,本来就比食堂高啊。”
他看我有所不解,继续说:“在食堂招待有标准,每月由办公室统一结算;但在外面饭店招待,都是由分管领导直接安排招待的,招待没有标准、陪餐人员一大帮,招待后由分管领导签字,抹抹嘴就走,到月底饭店老板就来找镇长要账。漏洞最大的是,有些领导还从饭店拿菜回家,账却记在镇政府的头上。”
我问,办公室为何不去结账?
老纪回答,办公室白主任也很为难,一是他们不让办公室安排,二是白主任也不敢过问,他们都是领导。
我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安排办公室制定《招待管理办法》,办法规定:上面来人接待原则在食堂,食堂接待不了,可以在外面饭店,但必须由书记或镇长审批;统一标准,统一陪餐人数,一律由办公室统一安排并结算。
办法出台后,当月招待费就降了一半。
还有一项改革,来自于老纪的建议。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年夏天,天气非常炎热,可是镇里老是停电。我看到老纪挎着工具包,扛着梯子,不时地到南山墙上去换保险丝。刚换上没多时,又断电了。
我气得不行,批评老纪:“你是干什么吃的,怎么老是断电?”
老纪这时已汗流浃背,用褂禁撩起来擦去脸上的汗水,笑着说:“负荷太大了,刚换上一根最粗的保险丝又烧断了,我先用铜丝接上。”
来电后,电风扇又重新地转动起来,我继续办公。可是,到了中午,刚吃罢饭,又停电了,原来那南山墙的线路被烧断了一大截,还差点酿成了火灾。
正当老纪上去查看时,从南院来了一妇女,趿拉着拖鞋,手指着老纪,嘴里不干不净地数落着老纪。
我站在办公室的阳台上,往这边看,那妇女似乎看见了我,然后大声地说:“书记镇长都是神吗?不怕热吗?为什么还让这个半边凑来修,牛年马月才能修好,俺大人孩子快热死了!”
我看老纪从梯子上下来,气得好像要与那妇女理论一番,我随机将老纪喊了过来。
老纪来到我办公室,我让他坐下先喝口水。这时,我发现老纪全身都已湿透,脸上的汗水随着脖子一直流向胸膛。
我问,刚才那妇女是谁?
老纪回答说,那妇女是副镇长老张的老婆,经常来镇院内说三道四、指桑骂槐。
我说,找供电站的人来修吧。
老纪若有所思地说:“供电站的人来,也修不好,因为负荷太大了。负荷大,大就大在前院,这个院所有家庭的线路都从镇政府总电表下连接的,他们从不出一分钱电费,不用白不用,他们冬天甚至烧电炉。夏天,家家的空调、冰箱等电器一起开,还有不烧坏线路的?”
我说,不行就改线路,前院单拉一条线路,各家装各家的电表,镇政府线路只用于办公用电。
老纪试探地问:“前几任领导都没改动,怕惹麻烦,书记,你决心要改?”
我坚定地说,一定要改!
老纪看我决心很大,狡黠地建议说:“要改,这样改,先不慌修,搁置它天把(指一天左右)。我对外就说修不好,让前院的人热燥起来,先降低他们过高的依赖性,然后倒逼他们同意改线路。书记,你也得坚持忍一忍,今晚我给你买个煤油罩子灯,先凑合着办公,明天下午再改线路。”
我说:“好,就这样做。”
我理解老纪的想法,他是在为我降低工作难度和压力。
老纪回到院内,收起梯子和工具包,悄没声息地走了,然后是杳无音信。
待我下村傍晚回来时,发现我的办公桌上多了一盏罩子灯。
老纪给我买的油灯
晚饭后,我点起了罩子灯,坚持在这昏黄的油灯下看文件。刚开始还对这久违了油灯有些兴致,但不多时,满身则大汗淋漓。我暗笑,这大概就是改革的代价吧,但“痛并快乐着”。
不一会儿,就听楼下院内有吵闹声,我站在阳台上往院内看,只见有南院住着的班子成员,有班子成员的老婆孩子,都在指责老纪不去修电。
只听到老纪说:“今天夜里我是修不好了,你们找书记也没用,你们看到没?书记都在点油灯办公呢。要修,也得明天修;供电站的人说了,要修,明天必须改线路才能修,不然明天也修不好。”
前院那些人沉默了两分钟,然后七嘴八舌地说:“无论怎么修,也得修啊,就是改线路,也得抓紧!”
老纪爽快地答应,明天一早就去找供电站。
那帮人走后,老纪跑到我屋里笑着说:“这事成了。明天上午就可改线路,可以提前半天。”
临走时,老纪说:“屋里热,来院内乘凉吧,茶水已准备好了。”
我和老纪坐在院内的长条椅上,默默无语,会意地对视笑了笑。虽然那一晚没电,但院内月光如水,风轻云淡,我心里觉得凉爽极了。
第二天上午一大早,老纪就带着供电站的人来改线路,不到三个小时就改好了,合上电闸,从此再无断电之扰,同时镇政府当月电费就降了三分之二。
这项不起眼的改革,在工作上,给我三点启示:一是改革要真调研、听真话。二是改革要瞅准时机,时机不到,改革的难度大、成本高。三是利用转机,烘托氛围,乘势快为。
几年与老纪接触下来,我与老纪有了较深的感情。
他有时送我一些新打下的绿豆或新摘下的茄子、辣椒,让我周日带回家;我有时也从城里给他带些糕果,从家里给他老婆孩子带几件衣服。
老纪家里的饭菜,平时很清淡,缺乏油水,我记在心里。
有时,我晚上在外面饭店接待上面来人,饭后,我就将饭桌上基本未动筷的一些肉和大馍带回来,有时剩下的半瓶酒,我也提回来,送给老纪。
当我看到老纪喝得高兴、吃得快活时,我心里也很欣慰。
一开始,镇里有的干部对我这样做法,很是疑惑,不理解,但我仍然坚持,只要老纪不嫌弃,一有机会我就给他带点吃食。
有时带得多了,老纪就拿回家跟老婆孩子一起吃。我看到后,心里又辛酸又高兴。
离开潼楼镇已20多年了,我每当看到保存至今的那盏油灯,我就想起了老纪的面相,就会想起那夜话时坐过的长条椅,就会想起他讲过的那些有趣的乡间轶事……